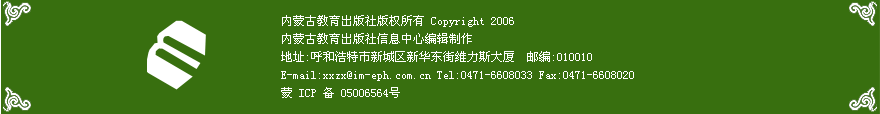“草原就像绿色的海,毡包好似白莲花”,“蒙古包的缕缕炊烟,轻轻地飘向蓝天,茫茫的绿草地是我生长的摇篮”,当听到这些悠扬深情的草原歌曲,人们总会有一种对于蒙古人居住的蒙古包的向往。
蒙古包是蒙古族传统的居所,是蒙古人勤劳智慧的结晶。实际上蒙古人称蒙古包为“格日”,可译为住房。现在所说的蒙古包中的“包”一词源于满语,意为“家”、“屋”。自清代以来,“蒙古包”一词以译音形式流传了下来,成为今天对于蒙古族传统居室的称谓。
蒙古包外观造型为圆形,且包顶为拱形,这样的结构很适于在干旱少雨、风沙大的高原气候居住。同时,建蒙古包无需打地基,只要选好位置架起蒙古包木制结构,覆以围毡拴系牢固即可。因此,蒙古包也是一种环保型居所,可以说它是依靠草场维系生产生活的游牧民族的最佳居住方式。
蒙古包以木、羊毛、马鬃、驼鬃为原材料,由木架、围毡、绳索三部分组成。据《黑鞑事略》记载,13世纪蒙古人的“穹庐有二样:燕京之制,用柳木为骨,正如南方罘思,可以卷舒,面前开门,上如伞骨,顶开一窍,谓之天窗,皆以毡为衣,马上可载。草地之制,以柳木组定成硬圈,径用毡挞定,不可卷舒,车上载行”。这是关于早期蒙古包较为翔实的记载。
蒙古包木结构包括陶脑(天窗)、乌尼(椽子)、哈那(墙面)、门、柱子等,其中陶脑是决定蒙古包大小、高低的重要因素。陶脑是蒙古包顶天窗,也是房屋中心位置,为拱形,宛如撑起的伞。蒙古人认为陶脑是家庭兴旺的象征,因此忌讳踩踏,且拆卸或建包时都是先从陶脑着手。乌尼指一头插或拴系于陶脑,另一头稍加倾斜系在哈那上端的数十根细木椽,多以松木为料。从陶脑斜搭下的乌尼犹如撑起的伞骨,又好像洒满大地的道道阳光。乌尼的数量取决于陶脑直径的大小。哈那的制作较为讲究,材料须选择韧性较强的藤条或木头,将其编制成网状,藤条交叉处使用毛绳拴系,因此具有可伸缩、耐用、不易断裂等特点。这样的哈那可根据气候节气以及需求调整其高度,改变包内空间大小。哈那数量同样由陶脑的大小决定。一般牧民家庭居住的蒙古包多用4-6个哈那,也有7-10个哈那的大型蒙古包,主要用于人数众多的宴会庆典活动。蒙古族视蒙古包门槛、门楣为家户开枝散叶的象征,禁止踩踏或触摸。如有踩踏者,会被视作是对屋主极大的不敬。在蒙古汗国及元朝时期,踩踏别人家门槛是要论国法处置的。13世纪初出使蒙古汗国的宋代使臣彭大雅曾记载:“国法中,踩踏门槛、打马头者当问斩。”有6个以上哈那的大型蒙古包中须有立柱。蒙古包里的柱子,主要起到支撑和调整陶脑的作用。粉饰以各类民间纹饰图案或雕龙刻凤的柱子,为蒙古包锦上添花,赋予蒙古包以艺术色彩。蒙古人珍视蒙古包柱,忌讳踩踏、跨越、环抱和依靠,迁徙时常将柱子和陶脑一起装车搬运,从不乱丢弃或焚烧。
蒙古包围毡是用白色羊毛做成,覆盖在陶脑、乌尼、哈那的外面。毡子具有保暖、不透风、不漏雨等特点。如果说蒙古包木制结构是其体,那么围毡就是其衣,衣附于体。一首“蔚蓝的天空下,碧绿的草原上,如洁白云朵般的蒙古包”的诗歌,惟妙惟肖地刻画出草原上“天高、地阔、人和”之景象。蒙古族自古以来崇尚白色,把白色当做高贵、纯洁、善良、忠诚的象征。《蒙古秘史》中成吉思汗封忠言相辅的兀孙老人以“别乞”官位并准许“骑白马,着白衣,坐在众人上面”。蒙古人常常以白色来形容心地善良之人,并将农历新年的第一个月称之为“白月”,至今有些地区的牧民仍然保留着夏季穿白色单袍的习俗。蒙古人崇尚白色的观念,同样体现在蒙古包洁白的围毡上。这不仅是蒙古族人民对色彩的审美取向,同时也是蒙古人向往幸福生活美好心愿的体现。
蒙古包绳索是用羊毛、马鬃或驼鬃编拧成的,用于拴牢围毡。尤其在寒冷的冬季把围毡系得牢固,围毡就会严严实实包裹着陶脑、乌尼、哈那等,抵挡住北方的严寒与风雪。在炎热的夏季还可以解开部分绳索,卷起围毡流通空气,来降低包内温度。因此,蒙古包的确是冬暖夏凉的好居所。
蒙古包的门一般设在南面或东南面。蒙古包内的设置、起居也有一定的规矩。自古以来,蒙古族视蒙古包中间位置为上座,其次为右侧,左侧居后。分配蒙古包内空间时,讲究“男右女左”。家中男子平日饮食起居及各类生产用具都要在右侧进行或摆放,而碗橱、挤奶桶等女子常用物品要放在包内左侧位置。蒙古包正中央的地方是摆放火撑的位置,包内北侧是主人、长辈或尊贵客人之位。西北侧是摆放佛像供桌的位置,这是蒙古包中最为神圣的位置,忌讳脚冲佛龛睡眠或将靴子、鞋袜之类摆放在佛龛附近。供桌前一般只允许僧侣或老人、孩子睡觉。
蒙古包易于搭建和拆卸,在拆卸时遵循由上而下、由外而内的顺序。拆卸后的部件可收在一起,只需一辆牛车或马车即可装载,非常适于逐水草游牧迁徙的生产生活方式。
古往今来,蒙古包承载了蒙古族艰辛的发展历程,也见证了他们所创造的辉煌文明,是蒙古族人民代代延续和传承着民族生命的家园。
网页编辑:孟春